刘欣|大家亦写“小儿书”:宋元理学社会化的视角
时间:2023/11/9 16:12:21|点击数:
宋元理学社会化是一场以理学作为哲学依据,追求个人、社会合理的政治生活秩序的社会运动。它不止于重新构建了完整的理学学术思想体系,也不止于提出了明确的理学政治主张,更在于它对作为现实生活底色的一般性知识、思想与信仰的塑造。理学社会化使理学思想从抽象的形而上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中,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规范和理由,成为他们“日用而不知”的文化底色。“小儿书”的编写就是打通精英知识与一般性知识隔膜的重要手段,是宋元理学社会化的一个有益视角。
“变化气质”:理学类“小儿书”的兴盛
“小儿书”又称蒙养书或蒙书,是中国古代专为儿童编写或选编,在小学、书馆、私塾、村学甚至自己家中进行启蒙教育的课本。它针对的是8—15岁(古人认为这是“童幼无知”的年龄段)的学龄儿童。“小儿书”是时代精神风貌和文化特征最真实的反映。
“小儿书”为儿童开蒙之用,长期以来学者对其不甚重视,甚至不将之视为学问。宋元理学家一改这种认识。他们认为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,通过“小儿书”可以让儿童破气禀之拘、人欲之蔽、物欲之惑,明理悟道进而变化气质。这不但是培养“新民”之基,更是成就“圣贤”之本。因此,众多理学大家积极投身到“小儿书”的编写中来。
著名的有吕祖谦《少仪外传》,朱熹《小学》《训蒙绝句》《童蒙须知》,杨简《蒙训》,程端蒙《性理字训》(又名《小学字训》),陈淳《启蒙初诵》,真德秀《教子斋规》,胡炳文《纯正蒙求》,陈栎《论语训蒙口义》,程端礼《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》;刘清之、彭龟年、王应麟、史浩、饶鲁、王孝友、许衡、吴澄等理学大家亦有“小儿书”传世。这一时期还出现了“小儿书”的汇编。例如熊大年《蒙养大训》就是将朱熹《训蒙绝句》、程端蒙《性理字训》、王柏《伊洛精义》等理学大家具有代表性的“小儿书”汇编成一册。元末朱升将方逢辰《名物蒙求》、程若庸《性理字训》(又名《增广性理字训》)、陈栎《历代蒙求》和黄继善《史学提要》四本书编纂合成了著名的《小四书》。
这些“小儿书”充满理学色彩,注重让儿童明白为人为事的道理,而不屑于以往“小儿书”侧重于识字和名物常识的偏好。吴澄曾说:“……周兴嗣《千文》、李瀚《蒙求》开其先,诵读虽易,而竟何所用?”王萱更认为“近世训蒙,率皆以周兴嗣《千文》与夫《补注蒙求》为发端,以其骈偶易读也。《千文》句以字集,或乖其义,识字累千,于事何益?《补注蒙求》句以事对,多失其序,事未易记,蒙何以求?”为了让儿童充分地理解其中的理学思想,理学家结合儿童的身心特质,在传统“小儿书”编写方法、形式和体裁上加以创新。如诗歌体的“小儿书”以诗歌来说明理学道理,虽然不像正规诗歌那样典雅华丽,甚至夹杂日常口语,但其内容浅白自然,朗朗上口,易于儿童明白其中道理。再如理学家根据儿童乐于形象思维、直观认知的特点,在小儿书文字部分配以图画,做到以图配文、图文并茂地揭示其中之理。
宋元理学类“小儿书”的大量出现,是理学社会化实践的必然结果。在“理气一元”本体论下,理学道德哲学沿着培育个体品质、同一家庭(族)生活伦理、进而在全社会确立共同的价值观的路径自然展开。在这一过程中“小儿书”成为理学塑造人的有力工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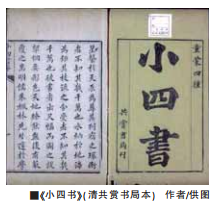
“圣贤坯璞”:“小儿书”的理学逻辑
在理学家看来,儿童天性善良,他们没有受到过多的物欲污染,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天地之性。所以朱熹说“古者小学已自养得小儿子这里定,已自是圣贤坯璞了,但未有圣贤许多知见”。璞者,被石头包裹着的未经雕琢的玉。朱熹用它来形容小孩子。而小学之教就是琢玉的过程,通过对小儿这块“坯璞”,“加光饰”“治光彩”,使之终成“玉”,为以后大学之教培养出“圣贤”打下基础。
针对儿童“心智未有所主”“德性未定,见闻未广”,其身心发育的不成熟、思维能力较弱等客观事实,理学家通过编写“小儿书”为其成长提供必要的引导。这种引导或是启发或是灌输。所谓启,就是教会儿童如何去思考问题。所谓发,是指帮助儿童掌握知识并能准确地表达出来。朱熹将这种教育方式比喻为春风化雨,“譬如种植之物,人力随分已加;但正当那时节欲发生未发生之际,却欠了些子雨,忽然得这些子雨来,生意岂可御也”。
人之初性虽善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界影响。儿童“知思未有所主”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,如果先接受了“异端邪说”就会排斥正确的知识和道理。所以理学家要通过“小儿书”先入为主地引导儿童,甚至不惜“生硬”地灌输理学思想,“虽未晓知,且当薰聒。使盈耳充腹,久自安习,若固有之,虽以他说惑之,不能入也”。当然,如果将深奥的理学道理用填鸭式的方法硬塞入小儿脑中,可能不但不会让小儿真正理解其中之义,反而使小儿感到义理过于抽象苦涩而心生恐惧,进而产生逆反的心理。因此,理学家在“小儿书”编写时力求浅白易懂,让小儿懂事、懂理就行,而非过多、过深地涉及其中的义理。“小学是直理会那事,大学是穷究那理”,“小学者,学其事;大学者,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”。
“圣贤坯璞”中蕴含的理学逻辑,深刻地揭示了圣贤可至可学这一蒙学教育目的。在理学家看来“性即理”,人的道德本性源于宇宙本体,天理至善人性必善,普通人与圣贤一样都秉持至善的本性,故而圣贤可至。圣贤可至却难至,缺乏自主判断的小儿更需要父母或师长的引导。无论是春风化雨的启发,还是填鸭式的灌输,在理学家看来“小儿书”是将“坯璞”变“美玉”的“法宝”。

“下学上达”:“小儿书”中的方法论
“下学而上达”出自《论语》,何晏解释为“下学人事,上知天命”。他将人的认识对象分为“人事”和“天命”两个层面,人事指日常随时发生,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事;天命是形而之上的天道。理学家在儿童的培养过程中,强调要先从日常生活的小事入手,反身切已进而理解天理。正如朱熹所说,“今使幼学之士、必先有以自尽乎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间,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之习,俟其既长,而后进乎明德新民,以止于至善,是乃次第之当然,又何为而不可哉!”
为此,“小儿书”强调从事中学、从做中学,即在“做事”中训练儿童最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。朱熹将小儿应学之事分为眼前日常生活中的事、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以及规范之事三大类。首先,通过日常生活中的“事”来培养小儿良好的习惯。“圣贤千言万语,教人且从近处做去。”《童蒙须知》中就有培养小儿良好生活和学习习惯的要求。如个人卫生方面“凡为人子弟,当洒扫居处之地,拂拭几案,当令洁净”,小儿的衣帽鞋子“自冠巾、衣服、鞋袜,皆须收拾爱护,常令洁净整齐”。东西要放好,“凡脱衣服,必齐整摺叠箱箧中。勿散乱顿放,则不为尘埃杂秽所污”。“文字笔砚,凡百器用,皆当严肃整齐,顿放有常处。取用既毕,复置元所。”小儿的言行举止要端正有礼貌,“凡为人子弟,须是常低声下气,语言详缓,不可高言喧闹,浮言戏笑”。“凡行步趋跄,须是端正,不可疾走跳踯。若父母长上有所唤召,却当疾走而前,不可舒缓。”学习习惯同样重要,他要求小儿上课时要态度端正、认真听讲。“将即席。容毋怍,两手抠衣,去齐尺,衣毋拨,足毋蹶。先生书策琴瑟在前,坐而迁之,戒勿越……坐必安,执尔颜,长者不及,毋儳言。正尔容,听必恭,毋剿说,毋雷同。必则古昔,称先王。”
其次,以历史上的人和事让小儿来明白是非曲直。小儿喜欢模仿也善于模仿,他们常常对自己仰慕的偶像充满了敬佩和羡慕之情。理学家利用小儿的这一特性,用历史上的人与事为小儿树立好道德榜样。如《小学》书中,朱熹于内篇《立教》《明伦》《敬身》《稽古》四卷引用古之圣贤为人为事之故事;外篇中的《嘉言》和《善行》两卷中收集了自汉代以来历朝历代贤人的言行。
最后,让小儿遵守生活中约定成俗的规矩之事。朱熹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特征,通过先教以事、后教以理的教学方式,循序渐进地使儿童从低向高,由浅入深地学习做人做事,最终是让小儿在这一过程中懂得并遵守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。让小儿通过生活中的事,学会并遵守事君、事父、事兄、处友的“礼”。这样才能逐渐从学做事过渡到明白义理,而小儿一旦“明理”并遵循它,规则就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自身的习惯和常识。
朱熹以后,朱门子弟如黄榦、陈淳、刘清之、魏了翁、真德秀,元代理学家许衡、刘因、吴澄等人都继承“下学上达”的方法和原则,并在各自“小儿书”的编纂过程中加以体现。元代程端礼在《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》中更是将“下学上达”的精髓加以光大,并运用于小儿的具体读书法。《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》明确规定了小儿不同期限及其主要的学习内容,还针对具体教学目标诸如如何写字、读书等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法,并创新出以“日程”作为学习效果检验的做法。
“下学上达”中所体现的理学教育方法是符合小中见大的蒙学教育规律的。小学阶段教小儿之事,虽知之浅而行之小,但培养受理学熏陶明德达理的新民,这一宗旨是不变的。正如朱熹所云:“学之大小,固有不同,然其为道,则一而已。”
教育是国之大计,教材又是教育之重中之重。它必然要体现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,古今中外概莫外之。宋元理学大家通过“小儿书”的编写,从本体论、目的论和方法论上构建了完整的蒙学教育体系,使理学的普及从“娃娃开始”,完成了理学全面浸润和培育“新民”的宗旨。这也为现今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编写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借鉴。
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宋元之际理学社会化研究”负责人、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刘欣
来源/作者: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任编辑:张雪




